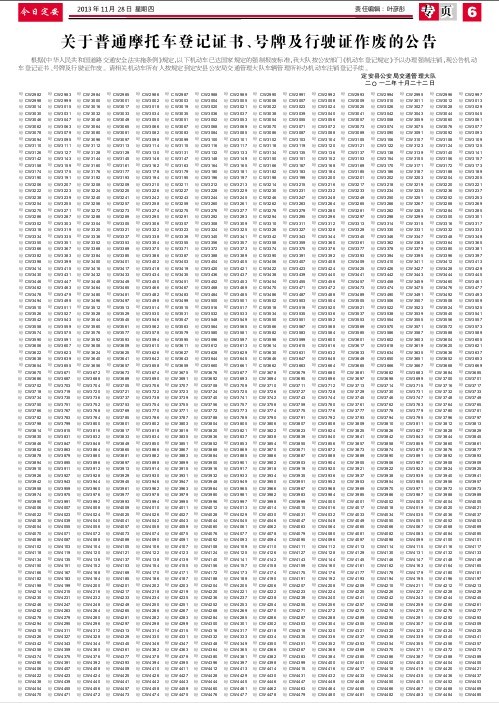7:文化苑
老屋听秋
一场绵绵细雨,让秋后的气温陡然降了下来。在温暖的巴山以南,仿佛总是需要出现这样一场雨水,清冷的秋意才会踩着季节缓慢的鼓点,姗姗来迟。
秋雨虽寒,却一点儿也不像夏天来得那么直截了当,而是欲言又止,仿佛内心里除了无尽的凉意,还有其他一些什么内容不屑于说出。但无论怎样,它所带来的变化都是显而易见的:大地上的事物都在收紧身子,退缩或失散;天空一夜间高了三尺,火热日头也渐行渐远。
又一次在村庄的早晨醒来,眼前已不再是梦中的景致。红瓦、白墙、楼房,遍地矗立,却留不住那些生动的交谈或零碎的吵嚷,就连鸡鸣犬吠也淡去影踪。回到渴望已久的宁静,夜里竟然数次醒来。这宁静,多么真实啊,让人清晰地听见自己的心跳,一遍遍敲打着幽暗、深远的夜。
屋子是土墙屋,床是木板床,甚至枕头还是谷物填充的内芯,只不过多了一股受潮的、沾满尘灰的陈腐气味。或许,由于常年无人打理,就连时间也会因寂寞而锈蚀、陈腐,仿佛停留于此的诸多物事一样,终究为我产生一段名叫陌生的距离。
辗转反侧中,一只老鼠骤然窜跳而过。无论如何,故地重逢,它的出现至少让死寂的空间有了一丝可爱的颤动,这多少让人欣喜。而如此情形也是难得的,老鼠的出现和消失,像烟花一闪而过,亦如断弦之音骤然响起,又带着意犹未尽的某种期许迅速褪去,只剩下轻薄微尘在身后缓慢沉落,直至归于无形。
此时,窗外仍未大亮。透过木格窗望去,有熹白晨光淡淡地穿过漫天轻雾,继而,又被雾气盖过一部分。停满灰黑尘土的木格窗台,由于被阳光和季风反复使用,已衰老得看不出本来面目,光线越是明亮地经过,越是对应出更多的空落。我不知道,这是它度过的第几个失魂落魄的秋天。孤独地朝着寒冬行去,它那单薄的跫音能否抵抗岁月的风寒?如果窗台挂满长串的包谷棒、红辣椒,哪怕风霜雨雪成群结队降临,也一定会充满亲人的温暖。
冥冥中,感觉到头顶的横梁不时发出“咔咔”的声响,像一个人筋骨的松动,又像一个人在昏黄油灯下翻开书页的微小动静。这个举足轻重的家庭角色,从来都是缄默无言,将家的幸福托举,把家的概念撑持,如今,终于发出一声叹息。这实在不能怪谁,经历年复一年的风吹雨打,时光又老了一岁,黄土、青瓦、木梁等等,也只好跟着衰退。
当年,我是这些声响的积极制造者之一。我可以无所顾忌地高歌、尖叫、跳跃,在屋子里跑上跑下、藏来藏去。我的衣裤、肌肤、呼吸以及幼嫩的心跳,和敦实土墙擦出火花,和凹凸地面碰出疼痛。那些黄的、灰的、黑的土质纷纷沾上衣裳、皮肤,呛入肺里,我也屡屡撞破它们的表皮。在这里,我花去大把青春的银两,却只买到一堆和自己较劲的回忆。回头一看,除了强大的时光,谁都没有讨到任何便宜。
如今,我成了一名恍若隔世的的旁观者。好在我的眼睛、耳朵和毛孔都能聆听——那么多声响依旧醒着,那么多事件仍然发生着,浓密炊烟还在缭绕着,所有亲人都在故事里活着。在足够辽阔的秋天深处,一座村庄尽管被掏空内心,仍然信誓旦旦地伫立原地,为远去的人守护鲜活的脉搏。
我相信,被青春岁月储藏的这些声响,被秋风吹打一次,压在心底的秘密也就像那探头的嫩芽,情不自禁地显露一分。
秋雨虽寒,却一点儿也不像夏天来得那么直截了当,而是欲言又止,仿佛内心里除了无尽的凉意,还有其他一些什么内容不屑于说出。但无论怎样,它所带来的变化都是显而易见的:大地上的事物都在收紧身子,退缩或失散;天空一夜间高了三尺,火热日头也渐行渐远。
又一次在村庄的早晨醒来,眼前已不再是梦中的景致。红瓦、白墙、楼房,遍地矗立,却留不住那些生动的交谈或零碎的吵嚷,就连鸡鸣犬吠也淡去影踪。回到渴望已久的宁静,夜里竟然数次醒来。这宁静,多么真实啊,让人清晰地听见自己的心跳,一遍遍敲打着幽暗、深远的夜。
屋子是土墙屋,床是木板床,甚至枕头还是谷物填充的内芯,只不过多了一股受潮的、沾满尘灰的陈腐气味。或许,由于常年无人打理,就连时间也会因寂寞而锈蚀、陈腐,仿佛停留于此的诸多物事一样,终究为我产生一段名叫陌生的距离。
辗转反侧中,一只老鼠骤然窜跳而过。无论如何,故地重逢,它的出现至少让死寂的空间有了一丝可爱的颤动,这多少让人欣喜。而如此情形也是难得的,老鼠的出现和消失,像烟花一闪而过,亦如断弦之音骤然响起,又带着意犹未尽的某种期许迅速褪去,只剩下轻薄微尘在身后缓慢沉落,直至归于无形。
此时,窗外仍未大亮。透过木格窗望去,有熹白晨光淡淡地穿过漫天轻雾,继而,又被雾气盖过一部分。停满灰黑尘土的木格窗台,由于被阳光和季风反复使用,已衰老得看不出本来面目,光线越是明亮地经过,越是对应出更多的空落。我不知道,这是它度过的第几个失魂落魄的秋天。孤独地朝着寒冬行去,它那单薄的跫音能否抵抗岁月的风寒?如果窗台挂满长串的包谷棒、红辣椒,哪怕风霜雨雪成群结队降临,也一定会充满亲人的温暖。
冥冥中,感觉到头顶的横梁不时发出“咔咔”的声响,像一个人筋骨的松动,又像一个人在昏黄油灯下翻开书页的微小动静。这个举足轻重的家庭角色,从来都是缄默无言,将家的幸福托举,把家的概念撑持,如今,终于发出一声叹息。这实在不能怪谁,经历年复一年的风吹雨打,时光又老了一岁,黄土、青瓦、木梁等等,也只好跟着衰退。
当年,我是这些声响的积极制造者之一。我可以无所顾忌地高歌、尖叫、跳跃,在屋子里跑上跑下、藏来藏去。我的衣裤、肌肤、呼吸以及幼嫩的心跳,和敦实土墙擦出火花,和凹凸地面碰出疼痛。那些黄的、灰的、黑的土质纷纷沾上衣裳、皮肤,呛入肺里,我也屡屡撞破它们的表皮。在这里,我花去大把青春的银两,却只买到一堆和自己较劲的回忆。回头一看,除了强大的时光,谁都没有讨到任何便宜。
如今,我成了一名恍若隔世的的旁观者。好在我的眼睛、耳朵和毛孔都能聆听——那么多声响依旧醒着,那么多事件仍然发生着,浓密炊烟还在缭绕着,所有亲人都在故事里活着。在足够辽阔的秋天深处,一座村庄尽管被掏空内心,仍然信誓旦旦地伫立原地,为远去的人守护鲜活的脉搏。
我相信,被青春岁月储藏的这些声响,被秋风吹打一次,压在心底的秘密也就像那探头的嫩芽,情不自禁地显露一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