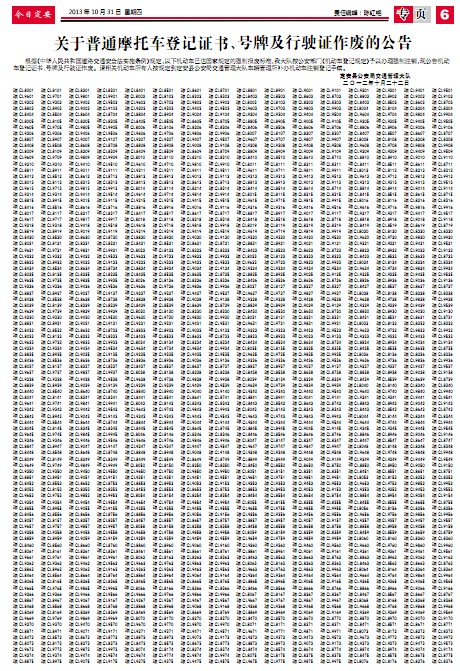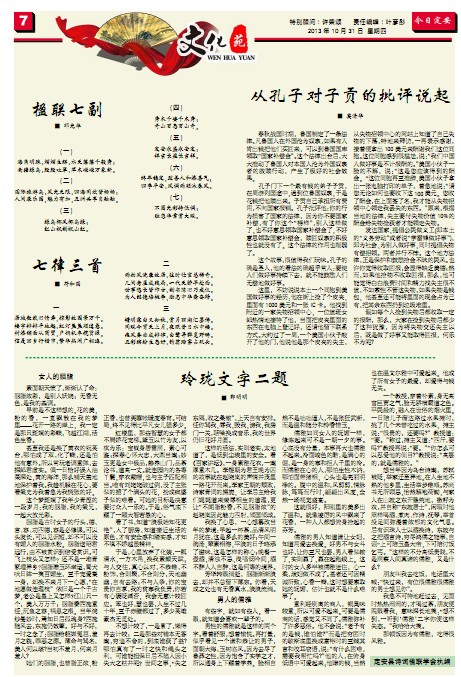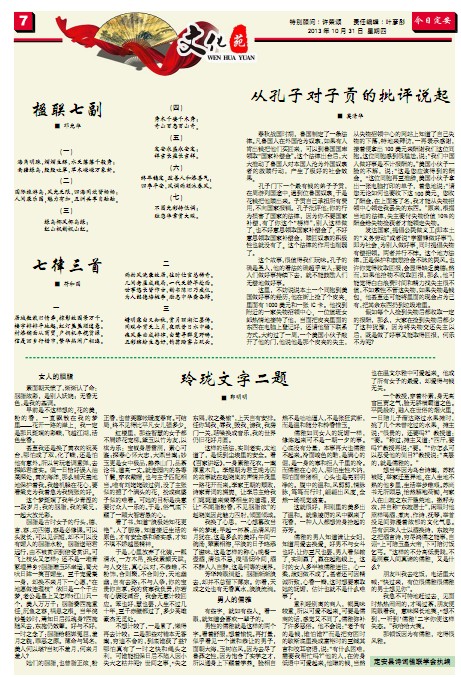
7:文化苑
玲珑文字二题
女人的胭脂
素面朝天惯了,渐渐认了命:胭脂浓彩,是别人妖娆;无香无色,是我的基调。
早前是不这样想的。花的美,粉的香,一直飘散在我的梦里——花开一路的岸上,我一定是那只斑斓的彩蝶,飞越江湖,活色生香。
甚至我还是换了黄衣的祝英台,哪怕成了双,化了蝶,还是怕他有意外。所以常玩老调重弹,去探郎君虚实。偶一日恰好误入油菜深处,黄的海洋,那么铺天盖地地保护着我。我趁机躲在花心,要看梁史为我着急为我慌张的好。
这个梦斑斓了我年少青涩的一段岁月:我的胭脂,我的梁兄,一起大放光彩。
胭脂是古时女子的行头,德、言、容、功四德,容是必修课。可以头发长,可以见识短,却不可以没有媚人的胭脂水粉。胭脂送昭君远行,由不被赏识到倍受赏识。可飞上枝头又怎样?还不是一堆青冢埋异乡?胭脂赠玉环幸运,蜀犬吠日眸一笑百媚生,三千宠爱集一身,却换不来月下一心愿,“在地愿做连理枝”依旧是一个千古梦,老公是皇上又怎样?江山只一个,美人万万千;胭脂委西施重任,沉鱼之容,祸患之根。当年浣纱曼妙时,焉知日后孤魂身?西施随风去,东施仍效颦。好与不好,一时之念了:胭脂给貂婵冤屈,羞月之貌,罪恶之源。薄命与骂名,美人何以堪?当初不羞月,何来月羞人?
她们的胭脂,也曾脂正浓、粉正香,也曾芙蓉帐暖度春宵。可结局,终不见得比平凡女儿强多少。
红楼里,那些智慧的女子都不屑娇花宠柳。黛玉以竹为友,以棋为乐:宝钗身居雪洞,素心可鉴;探春心怀大志,大鼎当案;妙玉更是女中极品,静养山门,品茶论书,道高一丈。就连园内的各等丫鬟,穿衣戴帽,也与主子匹配相当。唯有刘姥姥破过例,没了主张似的插了个满头的花,扮成疯婆子似的难看。可她的目标是决意要讨众人一乐的。于是,俗气底下藏了一颗大智若愚的心。
看了书,知道“淡极始知花更艳”,入了厨房,知道接近生活的原色,才有安全感和踏实感,才知不嗔不娇越显精神。
于是,心里放弃了化装,一瓢清水,一方木帛,换我素颜天赋;与人交往,真心以对,不恭维,不粉饰,合则聚,不合则分,天地幽幽,自有去路;不与人争,你的宝贵你自享,我的贫寒我负责,你若有心褒贬臧否,我会无意计较回应。笨也好,慧也罢,人生不过几十年,三千赤壁都过了,多少英雄豪杰无觅处。
不想计较了,一是累了,懒得再去计较;二是那些对错本无答案,穷追不舍的,到底谁获了益?哪怕真有了一时之快和绳头之利,可谁能担保日后不陷入因小失大之枯井呢?世间之事,“失之东隅,收之桑榆”,上天自有安排。任你骂我,辱我,毁我,谤我,我房门一关,聒噪换成音乐,我的世界仍旧花好月圆。
这样的活法,实则老实,太地道了,是低到尘埃里的安全。看《百家讲坛》,一身素雅花衣,一案厚重木几。李煜朝为君王晚为囚的故事就在赵晓岚的声情并茂里一路花开而来。李家王朝的颓败,诗家青词的旖旎,让李后主给我们娓娓道来荣辱相生的道理,更让“不闻脂粉香,不见胭脂浓”的赵晓岚因此魅力四射,倾国倾城。
我换了心思,一心想篡改当年的梦境:早起一杯茶,品清风明月犹在,这是多么的美好;午间一碗汤,荤素相溶,平淡的日子略添了滋味,这是怎样的称心;晚餐一壶酒,清浊不忌,浅唱低吟间,酒不醉人人自醉,这是何等的境界。
芳华转眼消逝,胭脂渐渐淡去,却并不总留下薄凉。你看,天成之处也有无香真水,淡淡流淌。
男人的儒雅
有些字,就如有些人。看一眼,就知道会喜欢一辈子的。
男性的儒雅就是这样的两个字。看着舒服,想着愉悦。再打量,似乎看见一个谦和恭让的男子,面朝大海,玉树临风。因为去尽了鲁莽之性,因为饱含了实学之才,所以通身上下藏着学养。脸相自然不是咄咄逼人,不是张狂武断,而是温和随分和怜香惜玉。
儒雅如同女人的妩媚一样,修炼起来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。心底没有分量,本事再大也儒雅不起来。冷面峻色的酷,是满心的倔,是一身的寒和拒人千里的冷。而儒雅在心的人,哪怕生性木讷,哪怕面带猪相,心头也是亮丽明净的。腹中的温和,风剪剪,情脉脉,笃笃而行时,翩翩出风度,全然一场视觉盛宴。
这就很好,阳刚里的美多出了温和。就像凌厉的风中飘来了花香,一种人人都想俯身拾起的芬芳。
儒雅的男人知道谦让女妇,知道用爱去换爱。好男不与女斗也好,让你三尺也罢,男人看似输了,实则赢了,赢在起跑线上。这时的女人多半被儒雅迷住,心一柔,泼妇做不成了。甚者还可因精诚所致,心香一瓣,这时想要索取她的妩媚,估计也就不是什么难事了。
重利轻别离的商人,铜臭味较重,所以可爱不起来。可要是儒商的话,感觉又不同了。儒雅弥补了许多恶俗。他不会说:“老子有的是钱,谁怕谁?”而是把穷困时的歇斯底里换成富裕时的三缄其言和咬耳窃语,说:“有什么困难,需要我帮忙吗?”他的人,在俯身低语中可爱起来;他赚的钱,当然也在温文尔雅中可爱起来。他成了所有女子的最爱,却爱得与钱无关。
一个教授,穿着朴素,身无高官巨贾之气,脸无骄横霸道之色。平民般的,融入在世俗的烟火里。一日陪儿子溜达路过水果摊时,挑了几个未曾吃过的水果,摊主说:“很贵的,还要吗?”教授道:“要。”称过,摊主又道:“四斤,要吗?”教授再说:“要。”“你怎么可以忍受他的侧目?”教授说:“高层的,就是儒雅的。”
想当年因为乌台诗案,苏轼被贬,举家迁至异地。在人生地不熟的他乡里,生活举步维艰。苏尚书无所顾忌,怡然解袍荷锄,与家人在山坡之东开垦荒地,撒籽为农,并自称“东坡居士”,闲暇时他照样喝酒、煮肉、作诗、抚琴,举首投足间弥漫着浓郁的文化气息。后有识珠人士以酒换诗,东坡与之把酒言诗,穷尽鸿儒之能事,自诩“上可陪玉皇大帝,下可陪讨饭乞丐。”这样的不分高低贵贱,不是洞察人间真谛的儒雅,又是什么?
朋友叫我去吃饭,电话里大喊:“快过来,有位很儒雅很儒雅的男士想见你”。
我急不可待地赶过去,见面时热热闹闹的,才喝过茶,朋友便睨眼看我,意味深长地笑:“想不到,一听到‘儒雅’二字你便这样失态。”我哈哈大笑。
那顿饭因为有儒雅,吃得很风雅。
素面朝天惯了,渐渐认了命:胭脂浓彩,是别人妖娆;无香无色,是我的基调。
早前是不这样想的。花的美,粉的香,一直飘散在我的梦里——花开一路的岸上,我一定是那只斑斓的彩蝶,飞越江湖,活色生香。
甚至我还是换了黄衣的祝英台,哪怕成了双,化了蝶,还是怕他有意外。所以常玩老调重弹,去探郎君虚实。偶一日恰好误入油菜深处,黄的海洋,那么铺天盖地地保护着我。我趁机躲在花心,要看梁史为我着急为我慌张的好。
这个梦斑斓了我年少青涩的一段岁月:我的胭脂,我的梁兄,一起大放光彩。
胭脂是古时女子的行头,德、言、容、功四德,容是必修课。可以头发长,可以见识短,却不可以没有媚人的胭脂水粉。胭脂送昭君远行,由不被赏识到倍受赏识。可飞上枝头又怎样?还不是一堆青冢埋异乡?胭脂赠玉环幸运,蜀犬吠日眸一笑百媚生,三千宠爱集一身,却换不来月下一心愿,“在地愿做连理枝”依旧是一个千古梦,老公是皇上又怎样?江山只一个,美人万万千;胭脂委西施重任,沉鱼之容,祸患之根。当年浣纱曼妙时,焉知日后孤魂身?西施随风去,东施仍效颦。好与不好,一时之念了:胭脂给貂婵冤屈,羞月之貌,罪恶之源。薄命与骂名,美人何以堪?当初不羞月,何来月羞人?
她们的胭脂,也曾脂正浓、粉正香,也曾芙蓉帐暖度春宵。可结局,终不见得比平凡女儿强多少。
红楼里,那些智慧的女子都不屑娇花宠柳。黛玉以竹为友,以棋为乐:宝钗身居雪洞,素心可鉴;探春心怀大志,大鼎当案;妙玉更是女中极品,静养山门,品茶论书,道高一丈。就连园内的各等丫鬟,穿衣戴帽,也与主子匹配相当。唯有刘姥姥破过例,没了主张似的插了个满头的花,扮成疯婆子似的难看。可她的目标是决意要讨众人一乐的。于是,俗气底下藏了一颗大智若愚的心。
看了书,知道“淡极始知花更艳”,入了厨房,知道接近生活的原色,才有安全感和踏实感,才知不嗔不娇越显精神。
于是,心里放弃了化装,一瓢清水,一方木帛,换我素颜天赋;与人交往,真心以对,不恭维,不粉饰,合则聚,不合则分,天地幽幽,自有去路;不与人争,你的宝贵你自享,我的贫寒我负责,你若有心褒贬臧否,我会无意计较回应。笨也好,慧也罢,人生不过几十年,三千赤壁都过了,多少英雄豪杰无觅处。
不想计较了,一是累了,懒得再去计较;二是那些对错本无答案,穷追不舍的,到底谁获了益?哪怕真有了一时之快和绳头之利,可谁能担保日后不陷入因小失大之枯井呢?世间之事,“失之东隅,收之桑榆”,上天自有安排。任你骂我,辱我,毁我,谤我,我房门一关,聒噪换成音乐,我的世界仍旧花好月圆。
这样的活法,实则老实,太地道了,是低到尘埃里的安全。看《百家讲坛》,一身素雅花衣,一案厚重木几。李煜朝为君王晚为囚的故事就在赵晓岚的声情并茂里一路花开而来。李家王朝的颓败,诗家青词的旖旎,让李后主给我们娓娓道来荣辱相生的道理,更让“不闻脂粉香,不见胭脂浓”的赵晓岚因此魅力四射,倾国倾城。
我换了心思,一心想篡改当年的梦境:早起一杯茶,品清风明月犹在,这是多么的美好;午间一碗汤,荤素相溶,平淡的日子略添了滋味,这是怎样的称心;晚餐一壶酒,清浊不忌,浅唱低吟间,酒不醉人人自醉,这是何等的境界。
芳华转眼消逝,胭脂渐渐淡去,却并不总留下薄凉。你看,天成之处也有无香真水,淡淡流淌。
男人的儒雅
有些字,就如有些人。看一眼,就知道会喜欢一辈子的。
男性的儒雅就是这样的两个字。看着舒服,想着愉悦。再打量,似乎看见一个谦和恭让的男子,面朝大海,玉树临风。因为去尽了鲁莽之性,因为饱含了实学之才,所以通身上下藏着学养。脸相自然不是咄咄逼人,不是张狂武断,而是温和随分和怜香惜玉。
儒雅如同女人的妩媚一样,修炼起来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。心底没有分量,本事再大也儒雅不起来。冷面峻色的酷,是满心的倔,是一身的寒和拒人千里的冷。而儒雅在心的人,哪怕生性木讷,哪怕面带猪相,心头也是亮丽明净的。腹中的温和,风剪剪,情脉脉,笃笃而行时,翩翩出风度,全然一场视觉盛宴。
这就很好,阳刚里的美多出了温和。就像凌厉的风中飘来了花香,一种人人都想俯身拾起的芬芳。
儒雅的男人知道谦让女妇,知道用爱去换爱。好男不与女斗也好,让你三尺也罢,男人看似输了,实则赢了,赢在起跑线上。这时的女人多半被儒雅迷住,心一柔,泼妇做不成了。甚者还可因精诚所致,心香一瓣,这时想要索取她的妩媚,估计也就不是什么难事了。
重利轻别离的商人,铜臭味较重,所以可爱不起来。可要是儒商的话,感觉又不同了。儒雅弥补了许多恶俗。他不会说:“老子有的是钱,谁怕谁?”而是把穷困时的歇斯底里换成富裕时的三缄其言和咬耳窃语,说:“有什么困难,需要我帮忙吗?”他的人,在俯身低语中可爱起来;他赚的钱,当然也在温文尔雅中可爱起来。他成了所有女子的最爱,却爱得与钱无关。
一个教授,穿着朴素,身无高官巨贾之气,脸无骄横霸道之色。平民般的,融入在世俗的烟火里。一日陪儿子溜达路过水果摊时,挑了几个未曾吃过的水果,摊主说:“很贵的,还要吗?”教授道:“要。”称过,摊主又道:“四斤,要吗?”教授再说:“要。”“你怎么可以忍受他的侧目?”教授说:“高层的,就是儒雅的。”
想当年因为乌台诗案,苏轼被贬,举家迁至异地。在人生地不熟的他乡里,生活举步维艰。苏尚书无所顾忌,怡然解袍荷锄,与家人在山坡之东开垦荒地,撒籽为农,并自称“东坡居士”,闲暇时他照样喝酒、煮肉、作诗、抚琴,举首投足间弥漫着浓郁的文化气息。后有识珠人士以酒换诗,东坡与之把酒言诗,穷尽鸿儒之能事,自诩“上可陪玉皇大帝,下可陪讨饭乞丐。”这样的不分高低贵贱,不是洞察人间真谛的儒雅,又是什么?
朋友叫我去吃饭,电话里大喊:“快过来,有位很儒雅很儒雅的男士想见你”。
我急不可待地赶过去,见面时热热闹闹的,才喝过茶,朋友便睨眼看我,意味深长地笑:“想不到,一听到‘儒雅’二字你便这样失态。”我哈哈大笑。
那顿饭因为有儒雅,吃得很风雅。